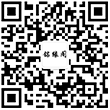人的乳名,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符号,甚至在孩子尚未出生之前,就已经被家中的老人或年轻的父母处心积虑地起好了。这个乳名或雅或俗,或状物,或抒情,或随口叫来。名与人水乳交融、相伴终生,须臾不可分离。
名字除了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生符号以外,还有着很强的时代烙印。例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叫解放、建国、跃进、文革、卫东等;农村人可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,许多老人随口给刚刚出生的男孩起诸如砖头、瓦碴、坷垃、石头、结实、铁蛋,或者按顺序叫大娃、二娃、三娃什么的,有的按出生月份起名,如叫正月、腊月;文雅些的便起个红旗、增产、丰收、凯歌等;则给女孩子随口起个诸如黑妮、丑妮之类的名字,好听些的则叫杏花、桃花、梨花,还有更省事的,直接叫大闺女、小闺女等。据老人们讲,随口起名字的这些孩子泼辣、不生病、好养活,不像现在的有些孩子这么娇贵、孤僻、自私、任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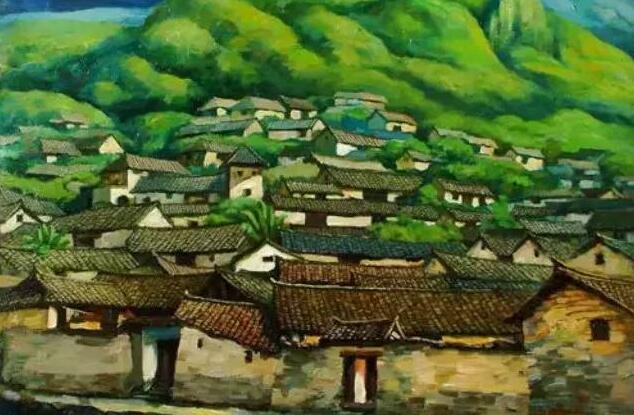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,刚实行计划生育那阵子,城里人多给女孩子起例如静静、颖颖、甜甜、娜娜等名字。农村比较开朗些的家庭,则模仿城里人给自家女孩子起些时髦的名字。重男轻女封建意识很强的人家,像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中一样,便给女孩子起招弟、盼弟、梦弟,盼望着抢生、超生的孩子是男孩,能传宗接代、光耀门楣、扬眉吐气。
因为起名字,还弄出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。在乡村,人们很忌讳孩子与长辈重名,就是古人所说的“为长者讳,为尊者讳。”村里有一户人家,添了个男孩后,找有学问的先生起了个名字,却跟同是街坊的一位老人乳名重名。老人的全家都极力反对,双方交涉多次都没有效果,等老人有了重孙子,便起了个同那户人家父亲乳名相同的名字,迫使他们主动将名字改掉,这件事情才算有了个了结。还有的孩子,在爷爷奶奶身边叫一个名字,到姥爷姥娘家,为了避讳与姥娘家族的人们名字发生“撞车”,需要姥爷姥娘重新起个名字,在小范围内传叫。
记得小时候,村里有位70多岁的老人种了一片甘蔗地,我们趁他中午休息时去地里偷甘蔗。心思缜密的他设下埋伏,多次挫败我们的企图,经常被他连骂带追,撵得作鸟兽散。败下阵来的我们不服气,随着一些大孩子大声连连呼叫:“小孩子、小孩子……”越喊老人越生气,叫骂得越起劲儿。后来才知道,老人乳名叫小孩子,他的儿子叫大亮,于是便有了“小孩子不小,大亮子不大”的笑话。现在想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当初我的女儿出生时,也经历过起名字的尴尬。被村里人称为“文化人”的我,绞尽脑汁,查了几天的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,愣是没有起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女孩名儿来。妻子至今还经常笑说给女儿起名字的难处:“香不行、臭不行,花不行、叶不行,俊不行、丑不行,红不行、青不行,绒子不行、棉子不行……”我们亲戚和家族中人的乳名,已经将这些字或谐音占尽了,稍有不慎,便惹得他们不高兴。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们,基本上都遇到过类似起名字的尴尬与窘迫。
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:“何处秋风至,萧萧送雁群,朝来入庭树,孤客最先闻。”萍踪絮迹,泪雨浸润。其实无论我们身处何地,只要看见步履蹒跚的母亲,或者听到稔熟的乡音乳名,所有关于名字的一切,都会成为对童年岁月的真诚感悟,成为对少年时代朴素清纯的抚摸和聆听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用高尚、饱满、丰蕴的人格去填补和治疗自己内心的虚弱、苍白与伪饰!